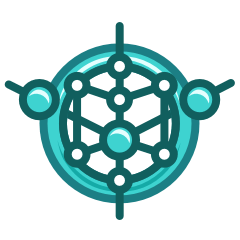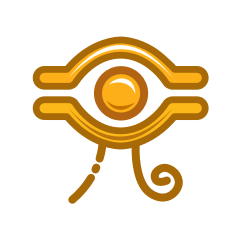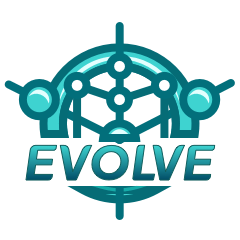译者 南·政
转载稿件来源于南·政B站专栏已获授权
前言:今天是奥古斯特·W·德雷斯的生日,转发这条消息到35个群,阿卡姆之屋就会送你一套《异乡人及其他》,我试过了,是假的,但今天真的是德雷斯的生日()
本篇原名《The God-Box》,刊于1945年诡丽幻谭。
译者:南·政
——2022.2.24
《神匣》/《神之箱》
(《The God-Box》)
By.奥古斯特·W·德雷斯

当菲利普·卡拉维尔(Philip Caravel)在他家附近下了地铁时,他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情。
“咕!他看起来不像一只吞下奶酪的老鼠吗!”当地铁开始运行时,一个曾与他同乘的乘客对另一个乘客说。
然而,卡拉维尔并没有听到,即使他听到了,也不会介意。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刚过黄昏,雾蒙蒙的下着细雨,黄色的雾笼罩着伦敦。空气中弥漫着秋天的气息,但卡拉维尔走在路上,就像在春天漫步一样,步伐轻快,心情轻松。他对自己非常满意,就像一个人怀有长久的忧虑,后来发现它们突然消失时的样子。他走起路来,仿佛置身于一层熟悉的保护壳中——伦敦的傍晚,它的味道被东印度码头附近的浓郁辛辣的香料气所点缀,泰晤士河上的游船发出柔声,汽笛与警笛的合奏声越发嘹亮。
即使看到他那肮脏的小房子,也没有影响他的情绪。
里面很舒适,家具也很有品位,虽然有点狭小。他几乎是轻柔的放下公文包,脱掉防水布,径直走向电话机,说出了电话号码,微笑地耐心等待着。他还是个年轻人,两鬓刚开始发白,**一张阴郁的脸和蓬乱的胡子。
一个声音说道。“喂?”
“科廷教授?”
“哦,是你。卡拉维尔。”
“你能来一趟吗?”
“现在吗?”
“事情很紧急,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你现在在忙什么?”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好吧,好吧。但我正在看一些关于阿亚-印加人的有趣论文。你不知道,我的孩子,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卡拉维尔有点不耐烦地说,“但是论文会等你的——而这个不会。”
卡拉维尔转身离开电话,意识到自己饿了。他朝公文包走过去,但又改变了主意。他走进自己的小食品室,拿着三明治和晚报,在房间里唯一一把舒适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不久,科廷教授来了。他的样子就像贝尔彻或克鲁克山克画的插图中那种心不在焉的人物。他的领带歪了,背心的扣子忘了扣,而他的圆顶礼帽,在他出门淋上雨之前,是需要掸一下灰尘的,现在却需要彻底清洗一下,这是它的主人无法做到的。他戴着一副被雨水冲刷过的眼镜,在镜片的背后是一双近视眼。他在门廊上取下眼镜,擦了擦,走进卡拉维尔明亮的书房。
“从你说话的口气,我就知道你在搞什么鬼。”他对主人说。“我想知道你还能瞒多久,你知道,这是一个平均的规律。”
“还有报应和惩罚,”卡拉维尔讽刺地说。“我去过索尔兹伯里¹了。”
“索尔兹伯里?”科廷坐下问道。
“这次只去了博物馆。”
¹:索尔兹伯里,英国威尔特郡小城,史前巨石阵所在地,也可以译成巨石阵。
年长的人盯着年轻的人;有那么一小会儿,他们俩谁也没开口。
然后,卡拉维尔把公文包拉过来,解开,拿出了什么东西。那是一个小铜匣子,四周用类似银或银合金的带子扎着。他把它放在客人面前。
“神匣!”科廷惊叫道。
“我想你会认出来的。”
“可是,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你确定没人看见你?”
“绝对。”
“你为它蓄谋已久!”
”我研究了这东西几个星期,然后我尽可能精确地复制了一份,虽然没有真正看到底部。把领带与复制品放在公文包里,我走了下去,出示了我的证件——毕竟,你知道,就连《纽约时报》也把我描述为一个‘崭露头角的年轻考古学家’——我被允许检查它。当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我只是把复制品换成了原件,现在就到了你手里。你想打开它吗?”
科廷教授脸色发白,往后缩了缩。“不。”
卡拉维尔笑了。“迷信?”
“随你怎么说。但无论如何,一旦被打开,它作为一件同类文物的价值就会降低。”
“我敢说,它可以被巧妙地修复。你不怕诅咒,是吗?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受了诅咒的。”
科廷教授看上去很苦恼。“我总是问自己,里面是什么?尘埃,或者是过去某个邪恶大师的什么可憎造物?”
"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你听起来像个讨厌鬼。"
“随你的便。事实上,卡拉维尔,这些东西非常古老。关于德鲁伊,我们仍未知的事情比我们知道的要多。”
“那么,这东西的德鲁伊起源是毫无疑问的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真正的‘神匣’——它是这种类似造物的总称,通常是封闭的,据说里面锁着任何神、精灵、小鬼、魔鬼、力量等等。因此,没有人知道古代德鲁伊祭司在他们的神匣里面放了什么,实际上,抛开神和魔鬼之类的东西不谈。我想,这肯定是设计得很危险的东西,是为了把好奇的人彻底拒之门外。把它翻过来,好吗?卡拉维尔?”
卡拉维尔照做了。
科廷调整了一下眼镜。“是的,传说是德鲁伊教的。”
“你会翻译吗?”
“好吧,大致说来——这里封印的是自外而来的某种东西,叫做修-迦兹(Sho-Gath),并非人类所能目见。破坏圣诵者必受可怕的灾难。它被交予魔匣的守护者。”
“那么是恶魔,而不是神?”
“至少不是仁慈的神。”他叹了口气。“现在你有了它,你打算用它做什么?”
“卖了吧,我想——就像其他作品一样。”
“总有一天你会被抓住的。”
卡拉维尔笑了。“等他们错过了这个,以及我留下的那个复制品,就不可能确定是谁拿走了它,即使他们记得我曾和其他人一起拿到过它。”
“不过,不管你做什么——我建议你不要动它。”
卡拉维尔把匣子在手里翻来覆去地把玩着。它的重量不错,但并不重。“这里面不可能有什么很大的东西——也不可能有太致命的东西。你有什么建议?毁灭天使粉(Powdered amanita virosa)²?”
²:Amanita virosa,毁灭天使菇,一种在欧洲分布的毒菌,白色的伞肉,幼年期形似鸡蛋,中毒者会在2~10天内死于肝功衰竭。不知德雷斯此处何意……
“我不是德鲁伊习俗方面的专家,他们只关心这些匣子里到底装了什么。”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它做得很漂亮。各种错综复杂的雕刻;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做成和它们近似的样子。幸运的是,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有些粗糙——粗糙到足以骗过警卫或其他旁观者。你认为我应该得到多少钱?”
“从谁那?”
“维特纳勋爵通常会买一些作为私人收藏。”
“至少要一千几尼。”
“很棒。”
“不过,整件事还是应该受到不雅的谴责。”
卡拉维尔笑了一阵。“不是吗?当然,除非你自己也很想要一件小东西。”在一片寂静中,他放下盒子,又转向老人。“ ‘魔匣的守护者’那句话是怎么说的?”
“这意味着其中一位牧师——可能是在索尔兹伯里,也就是匣子被发现的地方——是这个匣子的特殊守卫者。”
“当它被搬到博物馆时,他并没有很好地履行他的职责,不是吗?”
“啊,那是为了防止它被打开,或者,如果打开了,那是为了弥补所造成的损失。大概他能控制匣子里的东西。这些原始的宗教信仰遵循相当一致的模式。然而,修-迦兹并不属于德鲁伊教;据我所知,是亚特兰蒂斯的。这是最令人好奇的。”
“是吗?”
“就好像那东西是无意中从海里或附近海域召唤来的一样。”
“你说它是一个实体,教授。这恶魔该是什么样?看看这个盒子的大小——大约三英寸长,五英寸宽,三英寸深——告诉我什么样的东西能塞进这样狭小的空间?”
“起码是原生质,我的孩子。”科廷含糊地说,无奈地微微一笑。
“你在胡扯。”卡拉维尔回答。“你要喝一杯吗?”
他们喝了一杯苏打威士忌,又聊了一个小时。然后,科廷教授把他的发现写了下来,然后就走了。卡拉维尔把他送到门口;雨下个不停,雾更浓了。他回到书房,又拿起匣子。一千几尼!他在强烈的灯光下检查着带子;上面有一些小小的刻痕,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它有一种旧银器失去光泽的样子,很可能是旧银器。他摇了摇匣子,里面什么也没有;因为它发出空洞的声音。他敲了敲它,选了一块素净的底部做他的实验。它依旧发出一种空洞的回响。如果几个世纪以前有人在里面放了什么东西,那它早就化为尘土了。他的一些老考古学家同行着魔的不是一点半点,卡拉维尔想着。
他上床睡觉了。
那天深夜,卡拉维尔被一阵低沉但却持续不断的敲门声惊醒。他啪地一声打开床头灯,才发现时间刚过两点钟。他站了起来,因为显然没有人帮助他,他沿着狭窄的小门厅走到门那儿,门上镶着一块三角形的玻璃。在夜里,由于外面的雾过浓,在他看来这片土地是暗黄色的。他走到玻璃前向外望去。
一位老人站在那里,头露在外面,肩上披着一条巨大的叶状纤细披巾。
疑惑不解的卡拉维尔打开了门。
“如果你在找布伦纳医生,他的房子就在隔壁两家,”他说。
他有些惊恐地看到,站在门廊上的那个人一定很老了;他的皮肤像皮革一样,皱巴巴的,紧绷在骨头上,所以他的头实际上比它应有的大小要小,他那灰色、稀疏的头发,令人难以置信地虬结着。
“我不是医生,”他又说。
那条披肩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不是一条披肩;这是一条长长的裹条,像寿衣一样。
老人伸出一只爪状的手。
“看在上帝的份上,进来吧。”卡拉维尔凝视着,结结巴巴地说。他被那只向他伸出的、手掌朝上的枯手吓得目瞪口呆。
“匣子,”老人终于开口了,声音嘶哑而刺耳。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卡拉维尔冷冷地说。
“匣子,”老人重复道。“把它还给我。”
那声音很可怕,卡拉维尔战栗着。他从门口退开,又说他不知道老人在说什么,然后关上了门。
外面的声音又响起来了,令人厌恶,难以理解,用同样晦涩的语调说着,仿佛很久没有发音了。
“我将等待。我对你誓绝,以科斯的名义(the Sign of Koth),不可打开它。”
他终究还是被观察到了,卡拉维尔想道。现在要做的是在那个老**去找警察之前把匣子挪走。他想起了自己为门面而精心建立起来的名声。要把这个匣子藏起来没那么容易,他锁上门,迅速走到书房,小心翼翼地把窗帘拉下来,然后大胆地把一盏小台灯放在房间中央。
他拿着匣子,考虑着该怎么办。要是他能直接去找维特纳勋爵就不会烦恼,只需对他的战利品幸灾乐祸就好了。科廷教授!但现在想这些已经太晚了,因为有个老人在门外等着。如果他还在的话。
想到这里,他又小心翼翼地回到了前门。透过玻璃,他的视线只能看见雾在那里凄惨地打着黄色的旋。他冒险打开门闩,环顾门框四周。什么都没有,到处都是雾。港口和内河船只的声音,雾笛的鸣响,以及东印度码头上传来的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冲击着他的耳朵,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他又回到屋里,再次锁上门。来访者不在使他更加惊慌。要是他直接去报警怎么办?他现在可能还在跟某个警察说话呢!
他急忙回到书房。
有一件事他可以做,也许比其他任何事都要快。警察会去找匣子。他不会马上想到去找匣子的各个部分,他可以把匣子拆开,并有效地把各个部分隐藏起来。唯一的问题是,他不能把它弄坏,而他的目标是把它重新组装好后,可以得到的一千几尼。
他头脑冷静,毫不迟疑地拿出工具,在台灯下坐了下来。必须先把箍子取下来,然后再把有榫卯的侧面取下来——因为它看起来是用榫卯的。因为带子的末端与盒子的底部是融在一起的,所以取下它们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它们相融处锯开。相信之后的第二次融合会掩盖他的破坏行为。
卡拉维尔毫不犹豫地把带子锯成两半,从匣子上卸下来。他一时好奇,揭开了盖子。不出他所料,匣子是空的。他眼前什么也看不见。
但是,等等——那个角落里半便士大小的黑点是什么?确切地说,是半克朗的大小。不,更大了——它在变大!那是一绺烟,一缕烟,一股稀薄的烟卷,从盒子的一角冒了出来。卡拉维尔扔掉了它,好像它烫到了他的手指。它和盖子一起摔落,躺在那里。他举起灯来照亮它。若沥青般漆黑的烟气滚滚而出——形成一个球,一团云,一根爆裂的烟柱,盘旋着,翻滚着。

修-迦兹
卡拉维尔退到桌子后面。烟雾已经弥漫了房间的四分之一——一半——这时,他看见从房间深处探出一双凶狠可怕的眼睛,一张狰狞可怖的面孔,一种超越人类认知经历的、令人发狂的恐怖东西!他嘶哑地尖叫了一声;然后他的关节就瘫痪了。他朝门口跃过去,但那股烟柱仍在膨胀着,燃烧着,正冲击着墙壁、天花板和地板,就像什么东西许久没有进食一样的,充满了恐怖的活力,向他扑来。
菲利普·卡拉维尔家被炸得支离破碎,即便是对一本正经的《泰晤士报》来说,也算不上轰动。很明显,只有爆炸才能造成这种情况,只有爆炸才能把卡拉维尔炸得粉身碎骨。那些更耸人听闻的报纸隐晦地暗示,最终并没有找到足够的碎片来拼凑成被埋葬的卡拉维尔的遗骸。但多亏了大都会警察,这样的谜几乎没有,他们掌握着谜底的钥匙。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东印度码头地区寻找***造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那附近制造爆炸,纯粹是偶然的,是不可能的。简单推理就能得出,菲利普·卡拉维尔显然过着双重生活,他的考古研究是他真正虚无主义活动的假面具。幸运的是,一定是实验出了差错,结果却这样迅速地解决了问题。
诉讼过程中唯一不和谐的地方是一名**歇斯底里的陈述,她一直在房子附近从事她那可怜的职业,结果房子破裂了。她没有看到火;警方没有说他们无法发现起火、火药或任何可引爆物的证据。但她看到了别的东西,她看见一个老人,披着一条长长的“披巾之类的东西”进了屋,不久又出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又大又黑”的东西,在她看来,在雾中这东西就像“一团巨大的烟雾”,比房子还高。它顺从地跟着老人径直走到人行道上,沿街又走了一段路。这时老人停下来,把什么东西放在人行道上,大声说了几句她听不懂的话——“不是英语,不是法语,也不是葡萄牙语”,——这些都是她从摸爬滚打的生活中学会的语言,于是那个“大黑东西”就“像漏斗一样”钻进去,消失了。随即,老人拿起他一开始放下来的东西,夹在腋下,拖着脚朝伦敦西南部的方向走去。
这就是索尔兹伯里的方向,这个巧合甚至比伦敦警察局提供的还要大。但他们没有能解释这句话的合适答案,让那个街头**闭嘴。科廷教授沉浸于印加文献中好几个星期,却明智地什么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