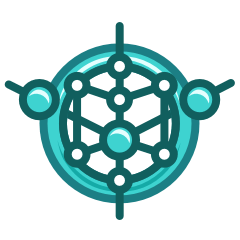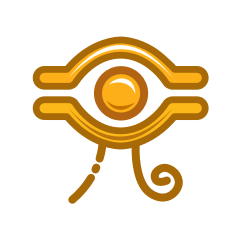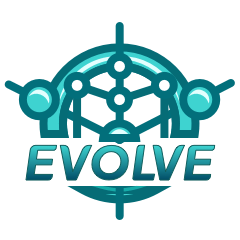译者 南·政
转载稿件来源于南·政B站专栏已获授权
前言:本篇原名《Chasing Shadows》,出版于1998年4月的《阿尔·阿齐夫》,本篇的作者小约瑟夫·普尔弗(Joseph S. Pulver,Sr),是重要的当代克苏鲁神话作家之一,黄衣之王神话领军人物,但不幸的是,他于2020年4月24日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去世,Pulver对黄衣之王神话体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不仅创作了30多篇相关作品,更是编辑出版了部分黄衣之王神话的选集。


译者:南·政
——2022.3.7
未经译者允许,禁止无端转载
《逐影》
(Chasing Shadows)
小约瑟夫·普尔弗
(Joseph S. Pulver, Sr)
他在寻找他失去的卡西露达。
双臂挥动,甚至没有估量奔跑者的行程。潮*与寒冷包裹着疲劳的电流。他的平衡在夜晚的监牢里并不值得信赖依靠,像拨浪鼓里的珠子一样摇动作响。他滑倒了,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风和伴随而来的雨被推开,或者可能只是被这个急转弯愚弄了。他充斥着微小的恐慌感,就像肮脏之物与他拉近了距离。他感到很冷,靠在墙上撑住自己,试图关上百叶窗,让自己的判断力和活力从他的身体里溜走。他害怕看向街道;远处的鹅卵石路面,现在满是汹涌的蓄水,顺着生锈的井盖冲向地下。
已经过去有一小时了吗?自从他离开了温暖的小酒馆与欢宴的欢声笑语后,他就宣泄般用尽了全身力气,在一种恐怖电影般的气氛下奔过城市。据他遇到那个肮脏的袭击者真的过了很久吗?
这危机的复杂性让他感到困惑。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对她怀念后想找个伴;仅仅只是一个微笑。或许一个声音就能让他动摇,哪怕只有片刻?但不是那种声音,不是那种恐怖而可憎的声音,就像充满诱惑的可怕秘密,并不适合教化过的人。
刮擦出刺耳的声音。在漆黑的巷子深处,有一种柔和的丁当声。也许是一只搜寻的猫打翻了罐头盖?——但愿如此!
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小巷的入口,小心地躲在阴影里靠墙站着。像乌鸦邪恶的曲调般强烈的风雨声,把其他的声音都逼得鸦雀无声。他的耳朵灵敏善听,但也不能辨别出脚步声。
因为他,激烈地饮着杯中酒——很快就收得了孤独——敢于吐出一首歌的歌词。他做了什么使那东西不安的事?只是唱歌吗?他的声音如何能在这难以平息的扣人心弦曲中传播得如此之远呢?
“该死的酒!混账的命运!”
那些话,她的话,又一次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奇异之夜升黑星,奇异之月循天际,但比奇异更奇异的,是
那失落的卡尔克萨。”
那溜走的该死雌狐——她的眼睛像夜空般漆黑的头发下一抹轻柔的、起舞的烟气。该死的她和她的虚假承诺;她教他这些话。去他的记忆吧,她那迷人的魅力,用她那丰满的嘴唇勾起他的欲望,用她那暖柔的手指在他的手腕上温柔地爱抚着他们的需求。除了她的记忆之外,他还需要更多的东西。
在那个寒冷蔓延的夜晚,他本应该和那个睁大眼睛的红发姑娘一起走的;她帮了那么多忙,只想要钱。但是没有。他只看了一会儿就移开了目光,另一个人就坐在那里。她熟悉地等待着,裹在过时的、一度优雅的淡蓝色织物里,孤独地躺在角落里,脸上露出最悲伤的表情。她是一幅他无法从她身上移开视线的肖像。他想像一个艺术家那样看待她:背靠柔软的窗帘,脚足抵着臀部,苍白的长胳膊抱着膝盖,美丽的下巴搁在胸前,嘴唇——没有亲吻——紧紧地贴在一起,几乎要哭了;一个害怕而孤独的孩子,脆弱,而美丽。她需要的是气息与灵丹妙药;一个他需要的。也许是由于酒馆昏暗的灯光,或者是他肮脏的欲望,比她的年龄长了许多年。它们并没有偷走她的美丽,只是给她染上了颜色。他的一切选择都破灭了。恣意畅饮,迫切和困苦,促使他去追求那更稀有、更柔和的花朵。
去他那折磨人的孤独吧,把他从他那肮脏的庇护所里推出来,那里满是厚积的尘埃与无灵魂的死的纪念品。该死的,在这个充斥着狂野雷声的夜晚,令人抓狂的挫折就像使人头晕目眩的东西。
他为什么要同意听呢?为何他要走进她温柔的花园,那声音就像第一次接吻的神秘和启示。如果她那双梦幻般的眼睛是那样的忧郁,那样的绝美,他想要拯救她,而且——什么?寻到一种恒久的魔力——守旧少女与受伤诗人急剧的渴望,找到了它就能得到救赎——为他们两人?
他想象着她身上的淡淡香水味还在,这迫切唤起了关于她那深情的吻的回忆。但他痛苦的呼喊打破了这一幻想,它在狂风中咆哮,以疯狂的插曲所具有的一切力量与姿态,穿过暴风雨覆下的街道。
那个男人怎么能——男人?不是男人!绝不是一个男人;他不会接受的。更多关于下水道或坟墓的东西,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又厚又乱,像害兽的皮毛。它怎么能追上他呢?他肯定能跑得比它快。更肯定的是,在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为什么它来了,而且一直跟着?他并不是他的狂影所讲述之子。一种卑劣的疯狂突然向他喷涌而出,他跌跌撞撞地冲进了汹涌的暴雨之中。原始的瀑布自由地扑向他,他飞快地航行着,颠簸着,冲进汹涌的过道。
他需要回家。在他的门,窗和墙壁后面用他的死物加固。它们坚定而不动。哦,它们痛嚎,有时像祭祀先祖般大声,但它们没有威胁或破坏;在许久之前被塑成后,它们就学会了循规守矩。
他靠在污秽的墙上,看着倾盆大雨,仿佛陷入了一种神秘的恍惚状态,他那不安的心情越来越浓,它充斥在他起伏的胸膛和飞快的眼睛里。家,他现在一定得回到家乡——现在。但是哪条路?那些满身污秽、步履蹒跚地穿过这片*透的荒地、肮脏的后街的穷人在哪?而且难以置信的干燥——就像从未改变过?
难道即使大雨滂沱,把毫无防备的街道扫得干干净净,也能设法避免这种来势汹涌的相会吗?那些聚集在一起的、刺人的小水滴,是不是被一定是从下水道里爬出来的、落魄而直立的危险——极有可能是疯狂的罪犯——吓坏了呢?
他做了决定,快速行动,像老鼠一样贴着墙向前走。
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坚固的门闩上了。他仔细察看了他那荒凉的回廊的墙壁与纪念品。仍然是一样的,什么也没动。没有一只手把它的意图强加在他那尘土飞扬的展示馆里。
他很快就脱掉了这件*衣服,生怕会把这疯狂的污点带到他神圣的旧家具和静态照片上。干了以后,他拿着瓶子里琥珀色的东西,竭力平息这场痛苦戏剧的不安。酒劲使他暖和起来,他的思绪转到昨夜,这一夜全是对她散发出的高贵美丽的梦幻回忆。
一次偶然的邂逅,就像世界上的这个人儿一样完美而精致,直到她溜走了。几天前?他看着那个暴雨倾盆的月夜,像所有被魔咒迷住的绝望的人一样,再次拥抱。他问她在半夜醒来离开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在酒馆里谈了一会儿。他们的话语像温柔的手指爱抚着。经过一番交谈,他把她带到了他的阁楼。他们之间有一种比言语和歌声更甜美的东西;它的词句不仅激动人心,甚至令人渴望憩睡。
她渴望听他演奏。
他打开满是灰尘的箱子。停了下来,背对着她。他能吗?他能触摸光滑的深色木头,让音乐像耳语一样流淌吗?他能给它一个声音,让这些故事像欢腾的仪式一样旋转吗?他知道她在等待。那是他的心与流逝的昔日,他把它献给了她。
不再是陌生人对陌生人摆姿势掩饰疼痛,他们互相对视着。他们之间经过的东西都在那间阴暗寒酸的屋子里。她站在里面;她是一个有福的,宁静的圣人,教导新生,拥有她所装饰的大教堂里所有的宁静祈祷。
她把长长的手指放在中提琴上,几乎碰到了琴弦。她抱着它,就像在《圣母怜子图》(Pietà)里的圣母抱着基督一样。她睁开眼睛,张开嘴唇,当她看着他的时候,他带着她的微笑。
“能请您为我演奏一曲吗?”
他无法拒绝。
他已经五年没有演奏了,但他是会为她演奏的。看着她的眼睛,他得到了灵感。她的微笑很温柔,他的缓慢乐章是一个苦乐参半的回答。
她说,她多年前看过他演奏,另一首让人感动落泪的歌曲。她记不起它的名字,但记得它那柔和的旋律。她承认,这暂时把她从悲伤和罪恶中解救了出来。她为他哼着曲调,然后开始歌唱。她的言语;词句奇异。歌词很适合这首奏鸣曲,就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适合一样;双方融在了一起——信任和激情点燃了——永久的,这一次连在一起,谁也不能独立。
这是玛德·斯科拉维斯(Mad Sclavi)创作的第十一中提琴独奏奏鸣曲,在他的妻子艾莲娜·塞西尔(Arienne Cecile)自杀后,他被送到皮法尔里(Pifarély)医生的精神疗养院;她扭曲的身体躺在阳台下,冰冷而丑陋,就像她绝望地抱了四个小时的死产婴儿。受折磨的斯科拉维斯,他们说他闭上眼睛流泪而逝。他们说,他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话是:“再见,白日。(Goodbye,day.)”

他为站在窗前的她演奏,她就像珍珠般的月光下的天使。他的天使吗?他拥簇着一个多么讨喜的谎言,像一个凄凉的十字架,悬在这个女人的面前,既缺乏又需要。她的翅膀能驱散长久的忧郁吗?难道他现在被唤醒了,又变得有价值了吗?第一段副歌结束,她跟着唱了起来——一个清脆、没有颤音的女高音;没有受过训练,但很杰出且柔和。巧妙地令人熟悉。流亡与死别(Exile and bereavement)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他入迷了。
这首精细而错综复杂的奏鸣曲忽高忽低。当旋律有时像波浪一样从痛苦走向平静时,会带来片刻的宁静。这首曲子是狂躁的欲望和错误犯下的一吻,它具有感染力,而且极其崇高。它的核心是悲剧性的考验和麻木的孤独。她的话既没有加重也没有改变它,它们是一面镜子。
“我的灵魂之歌已然拒殒——
我的声音,来自冰冷、脆弱的孤独,
将要干涸,回荡着破碎的心跳
伴着每一个汹涌的波浪,在那岸边
在那失落的卡尔克萨”
四目相吸,她唱,他弹。
奏鸣曲轻柔地结束。他把中提琴放回镶着薰衣草衬里的匣子里,她向他走来。他们站在被剥落的窗玻璃蚀刻的月光下,然后拥抱在一起。她的**像纯洁的月亮——苍白的奇迹使他屏住了呼吸,抚摸着他的心。他想他要落泪了。
她做了。
他们互相索求着对方的爱意(They made love),他的呼吸给了她生命,她又将这生命交予他。有一段时间,他被某种他能感觉到但无法定义的东西所拥抱,沉浸在诗人歌颂的狂喜之中。可是,雷声一响,大雨倾盆而下,就像狂奔的猎狗,伸出迅疾的脚步,追赶那滚烫的鲜血,她逃走了。
他想叫出声来,但**发干,不听使唤。他困惑地站在那里,门关上了,她的想象也停止了。就像永恒等待的漆黑,他没有颤抖,也没有移动,而时间的移动就像一个人在画廊里被庸俗作品所打动的疯狂行为一样。注意力又集中了,就像干渴、针刺或惊慌的老鼠噬咬一样,它是锋利的。她不可能离去的,不会是现在。然后,在雨中,他冲在她后面,迅速地移动,像一种苦难,迅速地占有它所经过的一切。穿过石头和路缘,穿过门口寻找,追寻着那淡蓝色墨黑的秀发。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但她的记忆,却在他心中温暖而索求着,不会消失。太阳流干了最后一滴血而垂落,他站在那里,低着头,在他的烦恼中,在他的窗前,看着长长的黑暗的雾气沉淀下来。自从他在雨中碰撞了以后,已经过去七天了。在沉重的负担下,他急迫的每时每刻都要精打细算。他怀着复杂的恐惧站在门口,在这难熬的时刻,他有两次几乎坚强得足以穿过这扇门。他背对着栅栏,像受惊的啮齿动物一样抽搐着。然后又对自己的局限感到沮丧——“要是能有另一个出口离开这个狭小之地就好了。”——他像一个在雾中搜寻的哨兵,发现自己站在窗前,呼吸结了霜。他的需求很简单,他希望自己是个危险人物,能够迫使他发誓出于恐惧而服从,要是他是不朽的就好了——这样就可以在月光下看到游行队伍,像奇怪的僵直腿的提线木偶一样摇晃着行进,在地下世界集会。在仪式上,他看到了有蜘蛛节肢的恶魔;宴会上怪诞的人头溅满自己的鲜血,扑通一声落在肮脏的盘子上;**的战士和萨满黑天使,发出古老的声音;他们在黑暗中鸾合时可怕的颤抖声,散布着散落的尸骨。他知道这头被污染的野兽出生在哪里。如果他是不朽的,他只会经过这里。
经过?不受约束与影响?
那个**疯子般的乱发,穿着疯子般大冬衣的怪物,一定是追赶到了别的地方。这个狂暴的动物,属于奇幻故事中一个比单纯的残酷童话更令人痛苦的故事,属于狼人的狂欢和混乱的阴影,一定是受到了某种其他的回响或可能的启发带来的冲击。是的,当然!事实是这样的;七天之后,某个无辜行人的步态肯定像一件华丽的服装一样引起了它的注意。
他砰的一声关上门,冲过去找她。他的心需要他唯一的地图。他的思想就像牙齿一样,张开又闭合,发出饥饿的呼喊。他需要她,只因在沙漠中迷失的男人把水变成了他的新神,只有她能救他。以全部的速度,他冲在冰冷的雨中。这条不舒服的街道,一连好几天都并非干燥,于是他换了另一条。一声痛苦的喊叫,不是针对他的,而是像魔鬼的笑声一样刺耳,唤醒了他对这个衣衫褴褛、肮脏不堪的人的恐惧。就在激动的喊叫声燃烧殆尽的时候,他不想要的记忆紧随其后抓住他的脚跟——那疯狂恶魔咆哮的回响。
笔直的街道拖着他向前,但是街角——那些等待着消除一切罪恶、麻烦和谋杀的十字路口——却成了最糟糕的未知数。他在每一片黑色面前都停了下来,内心充满的不是不安的细小蝴蝶,而是沉溺般的死寂。死亡会悄无声息地降临在秃鹰的翅膀上,还是会像火葬场的狂怒的心,像热辐射的嘶吼声一样汹涌而来?然而,由于他相思的进取心,他没有退缩或逃跑,他勇敢地面对每一场冲突。最后他来到了终点,他们相遇的酒馆里响起了一阵哄堂大笑,但却没有她。他独自走着。许多窗户里的光线已经消失了。无边的黑暗像无人停泊的岛屿一样,在日渐缩小的房屋和凄凉的地段之间的洼地上飘荡。挂着铁链网面纱的商店变成了空仓库和扬起的风。迷失在这个世界里。他被它的重量弄得不知所措。他踱来踱去,很快就厌倦了兜圈子。
这时敌人就在他身边。
“你已经迷失很久了,泰尔(Thale)。”
那不是他的名字,他知道这一点。那它是什么?或许是辕(Thill)?但不是——泰尔?然而,它听起来就像一首弹得很好的老曲子,只是用错了地方,那不是他的名字。不,这个被唤醒的幽灵弄错了,他确信无疑。但它很熟悉,正好符合他记忆中落下的空洞。
为什么?
他差点就开口了,却选择了逃跑。他必须;这种孤独与疯狂的气流一起沉重,散发着旋风和哀号的篝火的气味——它们像烈酒一样在他的呼吸中。在第一个拐角处和第二个拐角处,他逃走了。穿过布满煤烟的小巷,小巷里到处都是垃圾和杂物。他脚后跟下的玻璃碎了。当他匆匆走过时,纸像受惊的东西一样飞来飞去。他跑得很快,越来越快。他必须再次寻找到家乡。
雾升起来,覆盖了人行道。逐渐变薄的建筑物失去了坚固性,逐渐后退。他匆忙迈开步伐。
家,他一定得回到家乡,他必须。但是哪个方向呢?哪条路?那一条,冰冻草坪上的黑色牙印像是酝酿着奇异的天气?另一条,一条狭窄的通道,穿过一排低矮的平房,两层楼的人们睡在街灯微弱的灯光下?他害怕一步踏错,便往左走——另一步,避开那一排排伤痕累累的门面,台阶和门廊像破碎的咽喉,窗户像裂纹的镜子一样。他像一段飘荡的自由笑声,在疾风中狂奔,在寂静的水坑中溅起水花,跳跃着,旋转着避开所有被抛弃的东西。转啊转,滑过弯弯曲曲的街道,就像一张笑的嘴。
停下来,看一看。移动,然后再次停下。向右,又向左。可怕的误判,让他一次又一次转向。又一次右转,进入死胡同。他退缩了,又继续前进。他周围的一切也在时时变化。再一次,像风中移动的雾堆,时厚时薄,有形状奇异的洞天——在动荡不定的不毛深渊。卷须像可怕的黑枝树一样出芽,只会折断脖颈。
他继续往前走,宛如故事和歌谣掠过沉睡的耳朵。
现在驱使他的不仅仅是恐惧。好奇心和一种微弱的类似于愤怒的感觉冲淡了他的思乡之情。再走一步,还是两步或四步——就像迷宫里一只不知所措的老鼠。在桥梁和松软的土地上奔跑。被雾困住,备受折磨,却仍在奔跑。当他推动着前进时,梯田和成片的杂草都被忽视了。无法识别的低语与僵硬沙哑的声音萦绕在他周围,就像无名之物写下的怪异俳句。又一步闪电般奔跑的步伐。可能是文明的氛围涌现而出,但最终却毁灭了。
他停止冲刺,稳稳地站着。紧紧握拳于身体两侧,闭上眼睛和嘴巴,抖了抖身子。精神分裂?大麻烟卷?还是发烧刺痛了理智,就像痛饮烈酒一般?是什么紧抓的扭曲使它的根像灯塔上的光束一样伸展?他还要在这种折磨下做多久的奴隶?
他继续前行。那些本该在很久以前就发生的事情,在他身边的晨曦湖面上静静地停留着。融化的雪水倾泻而下,留下了依稀的印象,一群目光茫然的吉普赛人在庆祝,他们唱着七首响亮的歌,唱着炽热的鲜血和掠夺的暴力,唱着刺耳的咏史诗。
他想起了一场充满了痛苦泪水的疯狂。它曾用多少滔天巨浪冲击过他?他拼命地跑着,他的头发和外套的边缘沾上了十一月的风中飘散的落叶。然后他看到了月亮,沉重的双生无光珍珠将暗淡的光泽低垂在天空。它们矗在他面前,把他照亮。他觉得他们只是向他发出了悲伤的问候。它们反映了一道催函,就像他来到了一座充斥着神秘力量的空无一人的修道院。
他的忘性消失了。
有一阵子他只是站在那里。
不久,星星出来了;黑色的星星。他听到了海浪拍击的柔声,他又跑了起来。家,他一定得回到家乡。但它坐落于什么阴影下。家,对它的需求就是一切。那是他肚子里的一条饥饿的蠕虫。

他跑着,白色的月亮跟着他。他停住了,他的奔跑似乎没完没了,毫无意义。他累了,坐了下来,背对着一个大都市,像一个黑色的茶壶躺在那里,仿佛一个杂乱的院子,里面有一堆大肚的火炉,还有像烟囱一样直刺天空的高塔,上面顶着女巫帽般歪斜的尖顶。柔和的风,带着被扼住的声音和远方的目标,虽然受到触动,但他仍一动不动地坐着——就像僵硬的心——刻印铭文的墓碑在午夜中起舞——然而他却像置于烈火中,感到光明。他屏住呼吸。
“心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乡。而你的心却因距离破碎。”
他顽固的敌人与他对视,就像老旧的锐利器械。
“你怀疑我是否是真实。”
他认得那声音,那双眼睛,尽管现在——就像他自己的一样——戴上了面具。他的追踪者的装束已经变了,肮脏的大衣换成了破旧的黄袍,但仍是那个追捕者。

“我知道你是混乱(turmoil),”他说着,没有从岸边的岩石座位上站起来。
“啊。”那声音就像棍棒击打在柔草上。
他们凝视了很久。一种是期待,另一种是难以理解的新词。
“有那么一瞬间,你渴望光明和运动。你被一首歌吸引了,我们转过身,你就不见了。”黄袍人说。
“去哪儿了?”一时糊涂,他记不起那另一个地方。
“在另一个世界追逐影子。”
正如他所说,他记起了那一天,记得那朦胧的音乐在他耳边回荡,记得他的脚是怎样随着那逐渐减弱的回声奔跑的,但他不再在乎了。
“卡西露达也失踪了一段时间,现在回来了。我们——”
“不,”他回答,抬头望着像成熟的梅子一样悬挂着的黑星,听着海浪永恒拍打着海岸的声音。“王朝可以再推迟。我还是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穿着长袍,戴着苍白面具的人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
泰尔没有转身。他闭上眼睛,听着海浪不断冲击的声音,那声音就像心跳一样。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