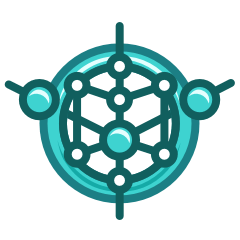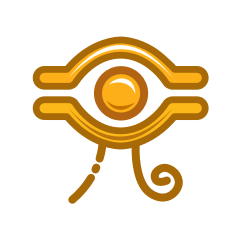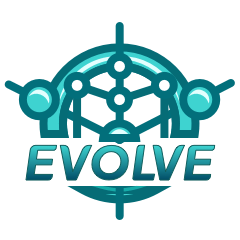译者 南·政
转载稿件来源于南·政B站专栏已获授权

译者:南·政
未经译者允许,禁止无端转载
《沃伦唐地下的恐怖》
(The Horror Under Warrendown)
拉姆齐·坎贝尔
(RAMSEY CAMPBELL)
那是我在伯明翰工作时,沃伦唐只是通往布里彻斯特路上的路标上的一个名字——我绕开了这条路,尤其是因为那里没有书店。我也不关心它的路线,经过沃伦唐路牌几英里,穿过克洛顿,这是一个小定居点,似乎基本上被遗弃了,少数有人居住的房屋挤在一条河的两岸,河的旁边矗立着一座混凝土纪念碑,它的雕刻被苔藓和风化弄得模糊不清。我一直都不喜欢乡下,充其量只是把它当作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的一种途径。现在,停滞几近匍匐的气味和笼罩克洛顿的寒冷薄雾似乎附着在了我的车上。这不受欢迎的存在让我更加厌恶科茨沃尔德的风景,农田和绿地遮掩了山上古老的岩石。我决定以后沿着高速公路从布里彻斯特往南开,然后再原路返回,尽管这要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不是格拉汉姆·克劳利,我永远也不会再靠近沃伦唐路。
在那些日子里,我喝酒是为了社交,而不是为了试图遗忘什么或入睡。每个月我都会遇到一两次业内的同行,我想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愿意代表儿童出版商,在我们就座时买一瓶巴尔蒂啤酒和尽可能多的拉格啤酒。每周六,我都会去金斯希斯的萨顿阿姆斯酒吧。在那些不需要被劝说的人当中结束我的一周,足以让我为下一周做好准备。但我想,正是在萨顿阿姆斯里,克劳利让他自己变得就像朋友一样。
我不记得这个过程的早期阶段,无论是他的情况,还是我以前认识的任何人。我渐渐习惯了在那个无装饰小酒吧里找他,那里的凳子、桌子和低矮的天花板都掺着麦芽酒的灰颜色。他会从大酒杯里抬起他那又宽又圆、胡茬丛生的脸,抽动鼻子和上嘴唇表示欢迎。当我走到他身边时,他会弯下身子,好像在他发出不可避免的嘲讽时,他希望我拍拍他的头或敲他。“她和七个小矮人在树林里干什么,嗯?”他会喃喃自语,或者“据我所知,你只会吹一种号角。难怪他要去追羊,”或者我旅行时所带那种书的其他引文。他的声音里有一种讨好紧张的情绪持续暗流,仿佛在为他说的任何话道歉,这也是我和他在一起从来都不自在的一个原因。我们聊着这一周的事,我在路上的事,他在当地蔬果店柜台后的事,我为他最新的两性通报做好了准备。真不知道这么多女人为什么会看上他,而且几乎没有一个能维持超过一次邂逅的。我对什么样的女孩会觉得他有吸引力的好奇心,可能让我愿意帮他的忙。
一开始他只是问我走哪条路去布里彻斯特,然后问如果高速公路关闭了我该走哪条路,到那时我已经受够了他躲躲藏藏的样子,仿佛一有麻烦的迹象他就会马上躲起来。“你想搭便车吗?”我问道。
他低下头,长发遮住了耳朵,抬头看着我。“嗯,你知道,我想,确实,是的。”
“去哪儿?”
“你不会知道的,因为那地方不怎么样。不过不远,对你来说也不算太远,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什么时候碰巧往那边走的话。”
最后,他把沃伦唐的名字说了出来,就像说了一个他不指望得到回答的问题一样。他那令人恼火的试探态度使我不得不反驳道:“下星期我就到地图上的那个地方去了。”
“下个星期,你是说下个星期吧。”他的脸抽搐得厉害,露出了牙齿。“我没想那么快。”
"如果你已经放弃了这个念头,我会原谅你的。"
“放弃了——不,你说得对。我要去,因为我应该去。”他猛地说道。
尽管如此,第二天我还是来到了他的公寓,并没有真想到要去接他。可是,当我按他的门铃时,他在拉着的窗帘下探了探鼻子,说他五分钟后就下来。让我一直感到惊讶的是,他正在啃着最后一点可能是生的早餐,穿着我从未见过他穿过的唯一一套西装。他抓着一个闻起来有蔬菜味的小箱子坐在那里,而我则专心地开车穿过高峰时段,驶入混乱的高速公路。于是我们不可逆地上路了,直到我注意到他抓着行李,带着我在酒吧里听到的那种坚定。“你以为会有什么麻烦吗?”我说。
“麻烦。”他又咕哝了一声,露出了牙齿,似乎在说,我已经明白了这么多,没有必要再问了,我几乎要发脾气了。“能告诉我是哪种吗?”我提议道。
“你猜是什么?”
“不是一个女人。”
“看,你知道。是比特·瑞克丝。是我害她惹上麻烦的,好像你没猜到似的。因为她让我走太快到没时间穿什么。没法压倒一个多毛的女人。”
这比我所能接受的要暧昧的多。“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我尽量简短地说。
“去年。那时候她就怀上了。之后就该生下来了,但我,你知道。你了解我。”
他紧紧地抱着行李,好像要把那股毫无意义的蔬菜味挤出去。“害怕她的家人?”我毫不同情地说。
他把下巴贴在胸前,但我还是听出了他在嘀咕什么。“害怕整个该死的地方。”
这显然是值得一试的,也是我继续走老路线的理由,只因我看见前面三条车道的车辆一直停到地平线处,警车沿着硬质路肩向出事的地方疾驰而去。我从马上出现的通道离开了高速公路。
弗雷姆罗德,所罗, 弗雷泽那,威特明斯特。路标上出现了一些古老的名字,然后是一条狭窄曲折的路,树篱围绕着车,很快就遮住了高速公路。乌云密布的天空下,阴沉的树叶似乎闷烧着;隆起的山背发出耀眼的绿光。当我打开窗户让蔬菜的味道散出去时,微风吹了进来,这是九月里出乎意料的寒冷,感觉我的乘客的紧张变得明显起来。他蜷缩在行李上,对着带刺的高高树篱眨着眼睛,好像它们是我引他进去的陷阱。“我能问一下您的计划吗?”我开口打破了寂静,这种寂静就像陈旧的风景一样坚韧不去。
”见她。看看她有什么,她想让我做什么。他的声音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完全停止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想知道他在想什么。“你为什么到那儿去?”这是我最想问的问题。
“比特·瑞克斯。”
这一次我理解了它,尽管他的发音似乎不相信这是一个名字。“她就是我们要谈的那位小姐。”
“我们是在卡贝治帕弛认识的,你知道,在那个咖啡馆。她刚从大学毕业,但她住在我家。”我担心这可能是进一步亲密细节的前奏,但他越来越不情愿地继续说,“她回家后一直给我写信,想让我去她家,因为她说我会觉得像在家里一样。”
“那你怎么想呢?”
他抬起头,仿佛在嗅着空气,然后就僵持着这个姿势。沃伦唐的牌子在柱子上有点下垂,沿着树篱晃进了人们的视野。他半承认半的感情对我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我踩在油门上的脚都颤抖了。“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的话。”
只有他的嘴在动,几乎没有张开。“没有选择。”
没有比这更让我生气的回答了。我想,他的意志就像他自己种的一颗蔬菜一样,于是车子就冲进了沃伦唐路。当我们离开那个似乎要指向地面的标牌时,我感到路两边的树篱那有动静,有几个站在那儿的人影绝对仍跳着跟在汽车后面。我对自己说,至少是我弄错了他们的速度。当树篱上粗糙的缝隙让我看到被污浊的天空压抑的绿色田野时,没看见什么人,也没有人能跟得上车子。我没有时间去想这些,因为从克劳利慢慢向前挪着脸的样子看,我可以断定,在前面一英里处,四周是繁茂的田野、起伏的黑色山丘,眼前的景象一定就是沃伦唐。
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我发现它是我最不喜欢的乡村元素之一,一堆无足轻重的建筑,离任何地方都有几英里远,但我从未经历过如此直接的厌恶。一簇簇的茅草屋顶让我想起了长满干草的沙丘,与其说是人类居住的证据,不如说是大自然无意识活动的证明。当我沿着倾斜的小路向它们驶去时,我看到茅草盖在茅屋上,就像头发悬在**的眉毛上一样。这条路一直延伸到村子的平地,我看到最外面的小屋都很低矮,好像已经倒塌了,或者正在陷进未铺路面的泥土里。茅草遮盖了它们倾斜的窗户,我不合理地抱着希望,以为这个村子可能会被遗弃。接着,最前面的小屋的门往里陷了下去,当我刹住车时,一个脑袋从门口探了出来,注视着我们的到来。
那是一个女人的头。在它缩回去之前,我已经看清了大概。我瞥了克劳利一眼,生怕他认出来了,但他对村子里让他感到不安的某个地方皱起了眉头。当汽车驶进沃伦唐时,那个女人又出现了,她在头上裹了一条围巾,比她的裙子遮得还要多。我以为她抱着一个婴儿,后来又觉得一定是某种宠物,因为当她突然古怪地走到路上时,那个小东西从她怀里跃入了小屋的黑暗中。她把围巾打了个结,把她那丰满而扁平的脸从围巾里探了出来,瞪着肿胀的眼睛盯着我的乘客。我很想调转车头,向大路驶去,但他把车窗放低了,所以我就放慢了车速。我看见他们的头互相靠在一起,仿佛天空的背面压着他们,把他们挤在一起。他们的动作似乎隐隐约约让人想起了什么,但当她说话时,我没能想出那是什么。“你回来了”。
虽然她低沉的声音本身并没有威胁的意思,但我感觉到他很不安,因为一个他显然叫不出名字的人认出了他。然而,他只说了一句:“你认识碧翠丝(Beatrix)。”
“我们都认识彼此。”
她连看都没看我一眼,但我无法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她红扑扑的脸上长出了几根粗毛;我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她的脸颊因为刮过胡子而显得粗糙。“你知道她在哪儿吗?”克劳利说。
“她会和孩子们在一起的。”
他的脸一沉,头也垂了下去。“有多少?”
“所有的醒着的。你听不到吗?我想就连他也能。”
因为这显然是指我,我忠实地竖起耳朵,尽管并不我担心另一种感觉的增强:我们进入沃伦唐似乎加剧了蔬菜的恶臭。过了一会儿,我理解了一连串高亢而有规律的声音——孩子们诵着某种公式的声音——我几乎和我的乘客一样感到了轻松。“她在学校里,”他说。
“那是她,回到了她注定要去的地方。”女人扭头往屋里瞥了一眼,一只大耳朵的一部分从头巾上垂了下来。“喂饭的时间到了。”她说着,然后开始解开衣服前面的扣子,从门口往回走,我仿佛瞥见门外有什么东西在光秃秃的地面上跳来跳去。“一会儿那下面见,”她对克劳利说,关上了门。
我发动了汽车,以能达到的最快速度穿过村子。低矮茅屋的窗户上,有许多面孔透过昏暗的边缘向我窥视,我告诉自己,正是里面的昏暗使那些面孔显得那么肥胖,轮廓那么模糊,克劳利传染给我的紧张让他们的眼睛看上去那么大。在沃伦唐的中心,有几座小屋,其中有几座我以为是没有招牌的商店,它们向大路挤去,仿佛是被后面的土堆逼着向前走的。土堆和小屋一样宽,但更低,上面盖着茅草或禾草。过了中心,建筑物更加低矮,不止一家倒塌了,还有一些杂草丛生,只有透过半遮半掩的无玻璃窗,隐约可见有人在活动,而且行动迟缓,这才表明那里有人居住。我觉得空气中腐烂蔬菜的甜味正以某种方式把它们都拖下去,就像它威胁着要对我做的一样,我不得不控制住自己的脚,不去踩油门。现在车子已经快驶出不到半英里长的沃伦唐了,我还没听清他们在诵唱什么,那些高亢的声音就安静下来了——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在唱赞美诗,尽管他们的语言似乎完全陌生。我在想我是否已经经过了学校,正准备告诉克劳利我没有时间原路返回,这时克劳利咕哝了一句:“就是这里了。”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现在我看到沃伦唐左手边至少五十码左右的地方,有一个高高的土堆,上面长满了茅草、禾草和青苔。我停下车,但把脚稳稳地踩在油门上。“你想做什么?”
他茫然的眼睛转向我。也许是他的眼睛转的太紧了,才使它们看起来几乎是从他的脑袋里冒出来的。“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受够了。我伸出手让他出去,学校的门摇晃着开了,仿佛我给了它一个暗示。门后站着一个年轻女人,除了一件长袖及踝的棕色连衣裙外,我几乎辨认不出她的样子。她身后的景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黑暗走廊的光秃地板上,至少有六七个小身体不安分地堆在一起。他们中的一些无精打采地抬起头,瞪大眼睛看着我,然后又安静下来了。这时,克劳利从车里爬了出来,挡住了我的视线。“谢谢你,你知道,”他喃喃地说。“你会从这条路回来,是吗?”
“这么说你准备走了吗?”
“等你回来我才会更清楚。”
“我天黑前就回来,你最好到外面的路上去。”我对他说,然后加速离开了。
我一直从后视镜看着他,直到树篱把沃伦唐遮住。由于路面不平,后视镜在抖动,但我看到他在我身后挥了挥他那只空着的手,把身体面向汽车,仿佛他要四肢着地去追我。在他身后,一个人影从门口跳了出来,当他转过身来时,她抓住了他。除了她那张大脸的轮廓看起来毛茸茸的,无疑是被头发勾勒出来的,我再也看不出更多的东西了。
她和克劳利拥抱在一起——不管怎么说,她的四肢紧紧地抱着他——当我把目光从这种亲密关系中移开时,我注意到学校的扩建部分曾经有一座塔楼,那些长满杂草的石头散落在村子的边缘之外。他们管不管自己的教堂,一个上过大学的人为什么要沦落到乡村学校教书,也不关我的事,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对克劳利有什么影响。我告诉自己,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不仅因为他们长得很像。他们一离开我的视线,我就摇下车窗,飞快地开着车,以便驱走车上那股沃伦唐的愚蠢而污浊的气味。
不久,这条小路把我带到了一个与主路无标记的路口。我把窗户关紧,疾驰穿过克洛顿的遗迹,它仿佛被阴暗的天空和漆黑河水的隐隐寒意淹没了。我没有放慢速度,直到我看到了前面的布里彻斯特,它的医院和墓地比越来越多的街道还要多。在这些街道上,我感到更加自在;在布里彻斯特这样的城市里,我从没有遇到过不幸,而且似乎也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尤其是在书店里。我把车停在下布里彻斯特边缘的一幢多层楼里,穿过人群走向我的第一个约会地点。
我的圣诞礼物反响很好——在当天最后一家商店,或许反响太好了。新来的经理,之前的二把手,不仅比她的竞争对手订购了更多的印本,而且在过早的节日气氛中坚持要我帮她庆祝她的晋升。一杯酒牵出了更多杯酒,尤其是因为我一定是在努力消除我离开克劳利和沃伦唐后留下的紧张情绪。当我意识到我需要大量的咖啡和食物时,已经太晚了。当我觉得可以开车的时候,这个下午已经过去了。
暮色像烟灰聚在蛛网里一样覆上天空。我从停车场看到布里彻斯特上空的灯光,突然消失在屋中。医院是一个闪闪发光的畸形骷髅,旁边躺着大片的骨头。就连停车场的荧光灯也显得不自然,我坐在车里想,我必须开车回去的地方看起来会有多糟糕。我告诉克劳利天黑前去接他,但天不是已经黑了吗?他会不会已经认定我不来找他了,自己有了安排?这几乎足以说服我不必再回沃伦唐了,但我对自己的怯懦感到一阵内疚,使我羞愧地朝那天上午的路线驶去。
城市的光辉在视野中消失了。几盏车灯向我照了过来,然后只有我的灯光探着蜿蜒在山峦之间的昏暗道路,山峦在黑暗中升起,仿佛它们不再需要假装沉睡了。路的弯道来回摆动,无法避开我微弱的光线。有一次,一个长角的脑袋透过一扇门瞪着,一边嚼着,一边转动着眼睛,就像它们要被宰杀时一样,愚蠢地转动着眼睛。我记得当克劳利准备下车时,他的眼睛是如何突出来的。
出了克洛顿,我被河水的寒意所笼罩。虽然我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但当我驶到第一个废弃的房子时,我听到了水声,水花飞溅的声音大得无法解释,除非有什么庞大的物体挡住了水。我开得很快,穿过狭窄的桥,经过那些无法看见东西的建筑物,等我能克服莫名的恐慌时,我已经开了几英里远,经过那条没有标记的车道,到了沃伦唐。
我告诉自己,我绝不能以此为借口食言。当我到达沃伦唐路标时,那路标似乎正被越发黑暗的压力在帮助地面把它拖下去,我把车驶离了主干道。即使我开着大灯,我还是不得不以这样的速度行驶,让我觉得汽车正钻进粘稠的黑暗中,现在看来,这可能正是它所期待的夜晚。弯弯曲曲的道路表明,它尽最大的努力也永远不可能到达沃伦唐。树篱上的荆棘撕扯着空气,在残破的草木丛中,有一个缺口让我看到了在肮脏田野中间,垂着头,暗中蹲伏着的农舍。尽管漆黑一片,却看不到一点光亮。
也有可能是停电——我猜想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无足轻重的村庄,停电可能很常见——但为什么沃伦唐没有人用蜡烛或手电筒呢?我安慰自己说,也许他们用了,只不过离得较远看不见。树篱挡住了我的视线,不让我多看一眼。这条路向下倾斜,使我产生了一种不愉快的想法,好像沃伦唐已经把它沉下去了,树篱也停了下来,仿佛被咬掉了似的。当我的车灯照到最外边的小屋时,它们的长毛头骨仿佛从土里探了出来。除此之外,在通往半毁的教堂的路上,没有任何动静。隐伏的蔬菜恶臭已经开始渗入汽车。我相当费力才把车开得足够慢,穿过整个村子,才找到我来这里的原因。茅草屋的边缘布满了阴影,我驶过的时候影子就会移动,好像每一间茅草屋都在把头转向我。虽然每扇窗户都漆黑而空洞,但我还是觉得有人在观察我,当汽车随着摇晃的车灯光柱沿着空荡荡的小路行驶时,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直到我感到呼吸困难。我似乎听到了微弱的、不规则的砰砰声——肯定是我自己不稳定的脉搏,而不是地下的鼓声。我开到教堂和学校的旁边,发现砰砰声加快,然后停止了。现在我已经离开沃伦唐了,但我知道无论我选择哪个方向,我都将回到大路上,这说服了我做最后一次调查。我把车转了个弯,几乎倒进了倒塌的塔上的一片杂草丛生的石块里,按了两下喇叭。
第二声刺耳的鸣声紧随第一声进入寂静的黑暗。什么都没有动,在我的大灯射出的凝固的光中,农舍的屋顶连一根茅草也没有。但我突然紧张起来,担心自己可能会引起什么反应。我慢慢地把车驶离塔的废墟,开始再次驶过沃伦唐,我的脚颤抖着踩在油门上,强迫自己控制车速。当我经过学校时,一个模糊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后视镜上,追赶着车。只是我在车里感到相对安全,这才允许我长时间刹车以便看到那张脸。那人影全身通红,仿佛全身上下都被人剥了皮,就在他猛的抬起手来抓自己的眼睛那一刻,我认出了他,是克劳利。难道他的眼睛总是对突如其来的光线如此敏感吗?我松开了刹车踏板,笨手笨脚地把档位换到空档,只见他的手垂了下来,但一动不动。为了叫他,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把窗户放下来。“你想来就来吧。”
我几乎没有听到他的回答;他的声音很模糊——哽咽着。“我不能。”
要不是他堵在路中间,我就有从他旁边过的空间了。我怒气冲冲地从车里冲了出来,狠狠地摔车门,那声音仿佛又激起了一阵低沉的鼓声,要不是我一心想甩掉那令人窒息的蔬菜味,我可能早就注意到了。“为什么不呢?”我问道,呆在车旁边。
“来看看(Come and see)。”
我并不急于看到更多关于沃伦唐的东西,或者说他。在汽车灯光的反射光下,他的脸看起来肿了起来,胡子茬比平时多,眼睛似乎令人惊愕地放大了,吸收了昏暗的光线。“看什么?”我说。“是你的年轻小姐吗?”
“我的什么?”
我无法判断他的语气是无法抑制的开心,亦或是恐慌,还是两者兼而有之。“碧翠丝,”我说,在异常的寂静和黑暗中,我的声音比我喜欢的要高得多。“是你的孩子吗?”
“没有这个人。”
“对不起,”我喃喃地说,不知道自己是否该道歉。“你是说碧翠丝。”
我不愿意用语言表达出我所猜想的她一定做了什么,但他摇了摇迷糊的头,迟疑地向我迈了一步。我有一种感觉,这让我非常不安,这让我无法注意到他慢慢靠近时喃喃的那个词,那使他都不太记得怎么走路了。“你在说什么?”我喊道,然后我的声音在寂静中畏缩了。“是什么荒谬的吗?不要紧。上车的时候告诉我一声。”
他停了下来,双手悬在胸前。他那突出的牙齿闪闪发光,我看见他在嚼东西——似乎瞥见他的嘴和肥壮的脸颊上带着一种绿色。“不行,”他咕哝着说。
他的意思是我们两个都不能回到车里去了吗?“为什么不能呢?”我大喊着。
“来看看。”
在那一刻,我对可能的求助再不感兴趣——但我还没来得及拒绝,他就转过身去,跳进了黑暗中。他迈了两大步,至少是抽搐了两下,走到教堂那无门的门口。过了一会儿,他就消失在没有灯光的室内了。我听到地板上的东西发出急促的嗡嗡声。然后,在我耳朵能听到的范围内,一片寂静。
我跑到教堂门口,那是我的车灯发出的微弱光芒所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克劳利,”我催促着他,想提醒他我不想再逗留了,但黑暗中唯一的回应是我呼唤的微弱回声,接着是无处不在的蔬菜恶臭。我又喊了一声,然后怒不可遏,冲向我的车。如果我还理智的话——如果沃伦唐的影响还没有在我脑子**深蒂固的话——我肯定会把我的熟人交给他自己选择的命运,赶出我的生活。相反,我从仪表板下拿出手电筒,关掉大灯,锁上车,回到那座腐烂的教堂。
当手电筒的光线在门口摇曳时,我看到这个地方比废弃的更糟糕。走道两边有十来张长凳,每张长凳都够坐一大家子人,但上面长满了青苔和杂草,显得臃肿不堪。但它们面前的圣坛已经被撬起来,靠在教堂的后墙上,露出石头的底面。我用光束扫过被亵渎的室内,瞥见斑驳的绿墙上粗糙的图画,教堂的阴影在墙上跃动着。没有克劳利的踪迹,他也无处可藏,除非他蹲在圣坛后面。我蹑手蹑脚地沿着过道看去,几乎一头栽进了一片比黑暗更黑的黑暗中。手电的光线及时地射进了原本应该是圣坛的地方的地道里。
这条通道很平缓地倾斜到地下,远到我的光线无法到达的地方。它和一个魁梧的男人一样宽,但没有我高。现在我意识到,当我听到克劳利消失在教堂里时,我的心一直不愿意接受的是——他的脚步声似乎退到了教堂无法容下的更远的地方。我让光线在教堂的长凳上晃荡,最后绝望地寻找着他,无法避免地瞥见墙上潦草地的画像,那是一群滑稽形象的不敬舞蹈,他们的耳朵和脚大得不成比例,肯定是假的。接着,克劳利从我的灯光几乎照不到的弯道后的通道里说话了。“下来,来看看。”
一股巨大蔬菜的味道般的恶臭从隧道里升起,围绕着我。我踉跄着,差点把手电筒摔到地上——然后我蹲下身子,跌跌撞撞地朝呼唤的方向走去。从克劳利的声音中我也听出了更甚于我的困倦,我似乎没有理由不服从,我的行为和周围的环境也没有什么异常。甚至连蔬菜的恶臭也合我的口味,因为自从我冒险回到沃伦唐以来,我已经吸入了太多这种味道。事实上,我开始只想被带到它的源头。
我弯下腰一直走到隧道的转弯处,正好看到克劳利的脚跟消失在前面大约50码的一个弯道上。由于我一直不愿去听,现在我看到他的脚没穿鞋——至少是光着的,尽管我瞥见他的脚似乎比任何男人的脚都要多毛。他在对我,或着自言自语地喃喃着,语无伦次:“翠叶明启。反刍之食……暗中之爪……噬之源宫。”我以为只是我的光线不稳让通道变得更窄了,但在我到达第二个弯道之前,我不得不四肢着地。在前方越来越陡峭的隧道里,我听到的鼓声再次响起,我想象着教堂墙上人物的原型们正在发出这种声音,它们在巨大的地下洞**跳舞,用它们畸形的足击鼓。这景象让我犹豫了,但从下面传来的另一种植物气息引导着我向前走,来到了克劳利的脚跟撤走的另一个弯道。我现在正在匍匐前进,心满意足地像蚯蚓一样在地上爬行。每当我的膝盖凸向前时,我伸出的手中的手电筒的光都会被前方的隧道淹没。地面上用脚敲鼓的咚咚声充斥着我的耳朵,我看到克劳利长满毛发的脚跟最后一次消失在手电筒光线的尽头,不是绕弯,而是消失在地下的黑暗中,太大了,我的光线无法看清情况。他的呢喃停止了,仿佛因为遇到了什么东西而变得沉默了。但我终于听到了我询问孩子情况时他给我的回答:一点也不“荒谬”。他告诉过我,孩子被同化(absorbed)了。即使这样,也不足以冲破隧道尽头等待着我的东西的影响,我迅速向前爬向地下的洞口。
手电筒的光束在我前方延展开来,尽力照亮高到看不见的层顶下那广阔的空间。起初,昏昏沉沉,再加上我脑子里的震惊和麻木,让我没有看清太多,只看见一大群赤身**的人影围绕着一个从潮*土地中拔地而起的偶像在空中跳跃、扭动。这偶像形似一个呈绿色的复活节岛雕像,蔓生的杂草掩盖了所有特征,顶端隐没在上方的黑暗中。接着,我发现在这群崇拜祂的人当中,有一个是克劳利,我开始辨认出那些面孔,它们的大眼睛在黑暗中凸起,野兽般的牙齿在畸形的嘴里闪烁着光泽。我发现,教堂墙上的涂鸦并没有夸张它们的形体,它们也没有穿着服装。偶像周围的地面上到处都是它们的后代,无数堆积在一起的身体,不可能有人类把它们以后代相称。我麻木地凝视着这个古老的仪式,这是任何阳光都不能忍受的——然后偶像移动了。
祂向我展开了一部分身躯,微微发光的绿色附体,如同破茧而出的巨大翅翼。当祂向我逼近时,并没有开口,却在诱惑地低声呢喃着。即使这样,我在恍惚中也没有被吓到;可当克劳利蹦蹦跳跳向我走来,一位渎神的祭司给我奉上一份邪恶圣礼,将使我与沃伦唐埋藏的秘密相连。这时,我心中的最后一丝健康与理智开始反抗。我沿着隧道跌跌撞撞地后退,让手电照亮后面可能出现的任何东西。
在通往隧道入口的路上,我害怕被人从后面抓住。不过,沃伦唐的每一个居民一定都参加了这个兽性的仪式,因为我没有遇到任何障碍,除了隧道本身,我从圣坛下爬出来,摇摇晃晃地穿过无光的教堂,走向我的汽车。当我不顾一切地疾驶出沃伦唐时,那些低垂着的村舍朝我抽搐着头皮,路边的树篱在空中竖起,好像决意要把刺围在我的周围。但不知怎的,我在昏昏沉沉中终于来到了大路上,我的本能使我从那里开上了高速公路,然后回到了家,倒在了床上。
我睡了一天一夜,就是这样的麻木。连噩梦也没能把我弄醒,当我终于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时,我几乎相信沃伦唐地下的恐怖是其中之一。然而,我躲开了克劳利和酒吧,所以在一个多星期后,我才知道他失踪了——他的房东进了他的房间,发现里面没有床,只有一堆被挖空的杂草丛生的土用来容纳一具身体——那一刻,我的脑袋遭受了一种超出人类头脑所能承受范围的真相的冲击。